我在北京逐梦演艺圈

一线城市,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来来往往,支撑着繁荣,就像一个永不闭幕的舞台。但在现实中,拥有梦想会被视为人的弱点,借梦想之名进行欺骗和剥削。
这是真实故事项目的第 583 个故事
故事时间:2017-2018
故事地点:北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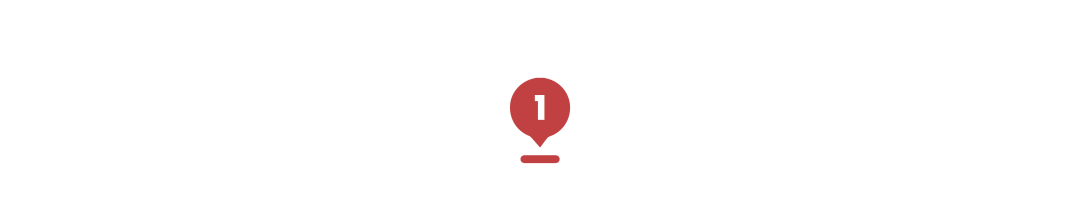
上午11点,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、三次换乘地铁,我从东五环到达丰台。从宋家庄地铁站出来,阳光明媚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我慢慢地走着,额头和手心全是汗。
在一家电影院的地下一层,我看到了白色月牙形的立体标识,旁边是大大的草书字:精诚戏剧社。
前几天,我在这里看了一场即兴喜剧表演。包括我在内,现场不到20个人,我坐在第一排中央。表演进行到一半时,演员的目光扫过我,与我频繁互动,甚至根据我的反应改变剧情走向。后来他们告诉我,这就是近距离即兴喜剧的运作方式。
谢幕时,一位身材魁梧、戴着黑框眼镜、面色白净的男演员站在最前面。他自我介绍说,陈逸松是该剧的导演兼编剧。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后在国家话剧院担任舞台剧演员。他做过一段时间的演员,但后来辞职创办了这家剧团,因为即兴喜剧是他的初衷。
陈总说,公司收入不好,快要没钱了。有一次,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,全场就只有一个观众,于是大家就围着小女孩,专门为她表演了一出戏。他的语气更加激动,眼含热泪,说,就算我们穷到每天吃泡面,就算只有一个观众,我们也要表演下去,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每个观众都笑出来。
灯光配合得很好,只剩下一束光,照在陈总的身上。我被他的演讲感动得差点哭了出来。他穷得连泡面都吃不起,却被梦想养活,长得那么胖。真是伟大的人啊!我心里想,照在陈总身上的,就是梦想之光。
我小时候也梦想过当演员。孙悟空是我当时的偶像,他长生不老,能变身七十二变,我很羡慕他。恨人类活不了孙悟空那么久,活了几十年就死了。我们能经历的人生真的很有限。看电视的时候,总是想象自己钻进电视里,参与到那些电视剧、动画片的剧情中去。
高考的时候,我报了好几所艺术院校的表演专业,但都没考上,最后考上了综合大学。大三实习的时候,我怀着演员的目标来到了北京,查了一下,北京大大小小的剧院有80多家,招聘网站上,有一家影视公司连续贴出了50多则招聘启事。演员缺口这么大,肯定有我能演的戏。
但来北京一个多月,我投递的简历全部无果。只有一次,一家在四会设有办公室的影视公司邀请我去面试。接待我的男士自称是徐先生,问了我几个“学校”、“专业”等问题,要求办理身份证登记,称公司包吃包住,新员工入职有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指导。
听说要我出示身份证,我怀疑这家公司的信誉,问:“你是表演系的老师吗?”他含糊其辞北京影视剧组招聘骗局,回避了我的问题,只是催促我交出身份证。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骗子而不是老师,然后转身走开了。
不工作的时候,我就会在小巷里闲逛,或者浏览售票网站,看看有哪些戏剧上演,然后挑选最便宜的戏剧去观看。
在诚信戏剧社,听了陈社长的慷慨激昂的演讲,我就萌生了加入他们的想法。
2017年9月14日早上,我再次推开剧场大门,演员们正在舞台上排练,一个留着胡子、皮肤黝黑的男人抬头看着我,问道:“你是来采访的吗?”
我点点头。那人领着我走到观众席后面,边走边自我介绍,他叫陆本,是副院长。还问我是哪里人,得到“东北”的回答后,他很激动,说我也是东北人。对了,你是哪里人?以后遇到什么困难,就来找本哥,别不好意思。
客套话结束,他推开了一扇暗门,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摆满了音响灯光设备和几把椅子,陈社长坐在里面,表情严肃,给人一种很厉害的感觉。问完我的基本情况后,他介绍了戏剧社的待遇,平时没有工资,年底根据票房收入和演员的演出比例一次性发放,食宿不包。他解释说,剧场租金很贵,门票收入无法覆盖成本,所以他得自掏腰包。不过,只要加入戏剧社,保证能学到东西。
社长得知我住在定福村,皱着眉头问我:“你真想进话剧社?要来就赶紧搬进来,我们每天早上八点晨练,然后上课、排练,每天都熬夜,我住得远,怕跟不上潮流。”我赶紧说我不怕起早,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广播站工作,每天都要早操。
陈校长让我明天去戏剧社,先试课一周,然后参加表演考核,考核通过就可以留下来,等会他们有话剧,我可以在这里看,最后还强调不用买票。
我感觉自己好像得到了某种祝福,高兴极了。坐在角落里,我开始幻想未来有一天,我能登上舞台表演:幕布拉开,灯光变换,演员们一个个登场。
两年后,我看到一段话,说人一旦有了幻想,就容易胡思乱想,容易执着,容易受欺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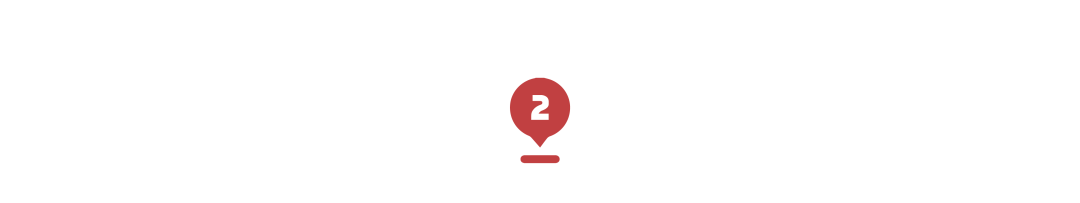
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忙碌生活,早上六点起床,坐三趟地铁去话剧社,做早操、上课、看老演员演出,有时还要负责卖票,一天下来,勉强赶上回家的末班地铁A班。
第一天进话剧社,我就犯了一个错误,在帮忙检票的时候,因为太紧张,把扫二维码的手机掉在地上,陈社长站在旁边训斥我:“你精神状态这么差,以后再也不行了,你怎么上台表演,我要你当女主角。”
我的心沉了下去。现在我成为女主角的机会已经消失了。
我偷偷问过一位女演员:“我会考核不合格吗?”她语气坚定地说,我一定会留下来,因为总统很喜欢我。
“真的吗?”我简直不敢相信。面试的时候,陈社长一直很严肃,我以为我没机会了。我问她怎么知道的。她没有正面回答,只是叹了口气,说她进话剧社才一年。我演的片子女主角不多,一直都是配角。
女主角叫英子,1990年出生,演不了主角,英子觉得自己输在了长相上,总裁总说她丑,只能演老太太、大妈或者搞笑角色,她个子不高,略显丰满,五官不算好看,但绝对不丑。但她毫不怀疑总裁的评价。
当时话剧社里有两个女演员,演女主角的那个女孩舞跳得好,说话轻声细语,气质有点像韩雪,另一个女演员叫珊珊,长得不怎么好看,患有癫痫病,社长不敢让她在台上表演太久。
上完一个星期的课,我心里想着校长说的绩效考核,就一直问校长:“我可以留下来吗?什么时候考核?”校长一脸淡然,随口答道:“可以。”什么都没说。就是绩效考核的事。
后来戏剧社来了两个新人,我发现凡是主动面试的,不管条件如何,都会被邀请去试听课,试过之后就会留下来。
我们的表演课分为三类。一类是主题表演,演员分成两组,每组给一个词,每组派一个演员即兴表演小品,最后说出主题的组获胜。一类是“喜欢和不喜欢”,每个人说出自己喜欢谁和不喜欢谁,并表演出自己表达的过程。喜欢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喜欢,比如亲情、友情或爱情,不喜欢可以是各种喜欢。还有一类表演课是解放天性,我们会模仿狗或猪,以及不同身份的人。
院长说,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活在世上,但我们表演的时候,要撕掉这些伪装,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,再把角色的属性运用到自己身上,这样才能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。他要求我们把埋藏在心底最不能说的秘密讲出来,这个过程就叫“撕掉面具”。
他演示了自己初恋女友的故事,她美丽纯洁,爱了他很多年,但是却背叛了他,让他很受伤,说完之后,他突然看着我说,我跟他的初恋气质很像。
我心里很尴尬,不知道他是想夸我还是想骂我,但他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。高中的时候,我为了初恋离家出走,结果他突然不见了,直到大学我才知道,他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。我讲了这个故事。
戏剧社的每个人都身上有伤疤,听完每个人的故事,大家都表示同情。轮到英子讲故事时,她一边哭一边说。
英子家住农村,有一个弟弟。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找不到存在感,她决心离开家。大学毕业后,她自学日语,去了日本。后来在一次“喜欢和讨厌”的表演练习中,英子说她讨厌我,因为我让她想起了哥哥。在家里,父母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哥哥身上,没有人爱她。自从我加入话剧社后,社长天天夸我演技好,眼睛灵动,腿长,就更不关注她了。
这位女演员名叫杉杉,因为患有癫痫病,在学校里被欺负,她自认为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,总是试图取悦别人,以免被排斥。她甚至会发出暧昧的信号,做出大胆的举动。在一次表演练习中,杉杉扮演一名妓女,其实她只需要象征性地拥抱和依偎,但她却伸手解开了男孩的裤子。
男孩很害怕,但总统认为她很放松,不惧怕舞台,并表示会帮助她实现表演梦想。
会长最喜欢看我们表演渣男出轨老婆、老婆撕破第三者、老公玩弄妓女的戏码,上表演课的时候,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样的戏码,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以前被女人伤得很深吧。
表演练习时,大家都很投入,尤其是经历过感情创伤的同学,在院长的指导下,我们以近乎宣泄的方式重复着过去的对话,然后认真地将其转化为对表演的热情。
有一次,我因为太投入角色,情绪失控,一巴掌打在了一个演渣男的演员的脸上,把脸打肿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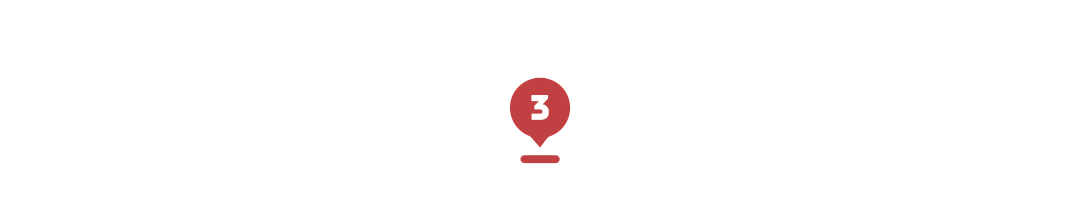
大学时,我报了一个表演训练班,班上是女老师教的,她教我们演员之间互相给予角色,要学会合作、付出。但校长的表演课总是把演员分成两组,形成敌对关系,鼓励大家互相抢风头。
我心里难受,但不敢质问他。院长性格强势,总是强调自己的专业权威,频频提到自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,上课问我们,演出时问观众,“你们看过《荆轲刺秦王》这个戏吗?我在片中演的就是秦王。”
我私下里向演员们抱怨道:“演戏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竞争?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
除了我之外,不管是老演员还是新人,都没有在剧组以外上过正规的表演训练班,在横店当过群众演员就是最高学历了。剧组和剧组都拒绝了,我几经周折才来到这里。
北京的大剧场不欢迎不认识的人,小剧场多集中在东城区,主要演实验艺术剧,不欢迎我们这样的演员,经常伸出橄榄枝的都是一些骗人的演艺公司,工商网站上根本查不到,剧社很多人都被骗过。
偶尔午餐时间,一些资深演员会聚在一起,讨论行业动态,分享手头的资源,并背着总统谈论哪里有演戏的机会。
说到演戏,最有经验的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。他从小练武,十几岁就开始演群众演员,演过不少小角色,但演了三四年,也没出名。他劝大家打消逃跑的念头。进话剧团的想法是,在剧组,你穿得脏兮兮的,吃得差,住得差。还不如进话剧社,至少能学表演,能上台表演,灯光一亮,还得体面点。
加入戏剧社的第二周,我就开始登台表演,虽然我饰演的只是一个小角色,但被观众注视和鼓掌的感觉足以让我兴奋一整晚。
我感受到站在舞台上的快乐,也希望观众们也能感受到快乐。是台下的观众让我们成功,让这部戏完整。我甚至理解了为什么总统在谢幕前总是要发表长篇演讲。一个演员渴望上台的时间永远比观众渴望他上台的时间长。
一个月后,老演员们突然集体离开了戏剧社,包括女主角在内,五个人同时离开,传闻离开前,不知为何和社长吵了一架,社长说他们是帮凶,太过固执,拿戏剧社当跳板,一个个都没有良心。
当时,社长根据老演员的特点,写了一个新的剧本,演出过好几场,很受欢迎。老演员们突然离开,他不得不向已经买票的观众解释。在台上,他郑重其事地说,演员们在话剧社学到了本领,现在有了更好的发展。虽然他舍不得他们走,但也由衷为他们高兴。
原定女主的离开,让英子嗅到了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。她拿着剧本问总裁,能不能让她演女主。总裁说她不符合角色的清纯特质,拒绝了。英子又问,女二呢?总裁还是摇头说:“她魅力不够。”
最后社长让我加急练习女主角的戏份,其他新演员也代替了老演员的角色,晚上赶不上地铁的男演员就住在社长家里,女演员则由话剧社出钱住胶囊旅馆。
第一晚排练结束,已经过了午夜,我们来到所谓的“胶囊旅馆”,发现那是一栋被打通墙壁的大房子,隔成三十多个小房间,每个房间3平方米,一张床又窄又小。房间之间的隔板没有与天花板相连,留有几十厘米的缝隙。站在床上,就能看到隔壁房间的人,男女住在一起。
会长租了一套两居室,他和女友住主卧,副会长和父亲住次卧,三个男演员睡客厅。其中一位在老演员离开后成功接班,成为节目的主角,成为社团的顶梁柱,开始掌管社团的资金和内部事务。
当时我很难接受七个人睡在一间房子里,但不久之后,我也加入了这种集体生活。
新剧紧张排练的两周里,我们每天晚上都练习到深夜,没有人抱怨辛苦,反而因为朝夕相处,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,我和几个住得远的演员,打算在剧院附近租一间房子。
2017年11月,我从东五环的小二居搬到了丰台更小的二居,和三个男孩合租,我们租了一套50多平米的两居室,离剧团俱乐部步行十分钟的路程。一个热爱演戏的富二代演员住主卧,付的房租最高,1800元。我的房间1200元,客厅有两张沙发床,两个男孩睡在上面,合租1000元一张。
签订合同那天,总裁也在场,他帮助我们和房东谈妥了条件,从1.6%的定金到1.1%的定金。
就连每月1200元的房租,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加入话剧社后,我并没有完全失去经济来源,只能靠妈妈偶尔的帮助。
搬进新家没多久,富二代的身上就起了满身的红疹子,排练或者上课的时候,他忍不住伸手去挠,检查后发现,都是房间里的小虫子咬的。
他没动,只是少去话剧社了,每天晚上还是等我们回家一起玩游戏。也许对有钱人来说,体验贫穷和演戏一样好玩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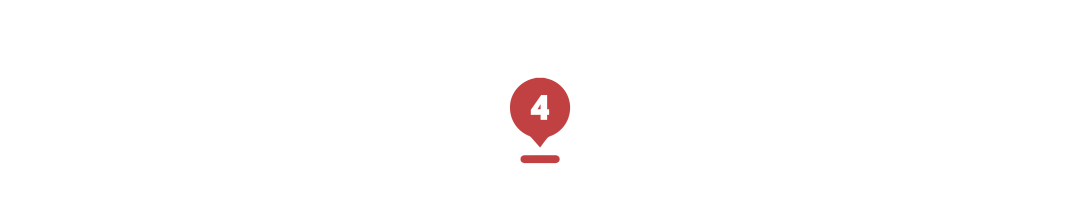
看一个人对梦想的渴望程度,要看他为梦想愿意付出多少。在一次聊天中,副院长陆本告诉我,他一开始并不想跟院长一起办话剧社,但院长找过他好几次,他没有多少钱,为了办话剧社,他哭过、闹过、扬言要在家里上吊,逼得父母赔他十万块钱。
副社长认为这是对戏剧社的一大贡献。我震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看出了我的惊讶,说:“嘿,幸好我现在有钱了。”
我干笑一声,剧团年年都亏本,他哪来的钱?
一天,一对衣着讲究的母女来看戏,谢幕之后,她们找到院长,指出剧情的逻辑漏洞。母亲语带善意,表示女儿现在读艺术高中,经常编剧,以后会报考相关院校。
总统鄙夷地看了她一眼,开始炫耀自己“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”、“国家一级话剧演员”的身份。女儿察觉不对,拉了拉妈妈的衣服,说: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我和演员们站在一旁,面面相觑。当晚的总结会上北京影视剧组招聘骗局,院长突然转移话题,攻击那对母女俩,说小姑娘上的是垃圾学校,什么都不懂。他说话时,目光威严地扫视着我们。空气异常安静,见没有人同意,他的目光又慢慢暗淡了下去。
当晚回到家,一个向来不喜欢八卦、睡在客厅的男演员突然爆料,问我们知不知道总裁身份是假的,查了一下才发现,总裁并不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,也不是国家一级戏剧演员。
爆料的演员和我差不多大,比我早半年加入话剧社,另一名演员补充道,话剧社没有社长说的那么穷,只是扣留了我们的钱,他看过电脑网站上的财务报表,还有剧院的租约证明,他怀疑这些钱被社长、副社长和剧院的主要支柱瓜分了。
我大吃一惊,问她们既然知道社长是骗子,为什么还要留在戏剧社呢?她们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我们找不到其他地方演戏了。”
我问谁知道这些事情,他们说上一批老演员因为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和没有片酬而离开的。
爆料男演员正准备离开话剧社,他和副社长一直在排练同一个角色,但每次上台他都演副社长,心里很压抑,很不平衡。
另一位演员选择留下。加入戏剧社之前,他在家乡做过手机销售员,梦想成为一名演员。现在他有角色要演,而且是总统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。他必须等待真正的机会。坚持不下去了就离开。
心想,我现在还是女主角,总不能就此放弃吧,内心深处,还是对舞台很着迷的,想先找份兼职,把简历发了几家公司,在新的简历里,我又加了话剧社演员的身份。
也许是我在戏剧社当演员的经历起了作用,这次有公司回复我很快,我在招聘APP上跟对方聊了聊,第二天早上就约了面试。
第二天,我向戏剧社请假,坐地铁去国贸面试。按照昨天的约定,出了地铁后,我拨打了对方给我留下的号码。电话接通后,铃声响了好久,却没有任何声音,有人接听。我连续打了五六次,最后一次,对方关机了。
我按照招聘APP上的地址去了,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地方,我惊呆了,又是一个骗局。
离职意向受阻,我又在剧院呆了几个月。第二年春末,剧院终于开始与演员分得票房收入。我分到了3000多元。我问院长为什么这么少,他说是因为我进公司头几个月总是迟到,所以被扣了点钱。其他演员的分也和我差不多,有些戏份少的演员也才几百元,赚得最多的是公司的顶梁柱,最高分到了7000多元。
没过多久,我又因为一场戏和副院长闹矛盾。那天,我在化妆间里和副院长对峙,化妆间里柱子突然从化妆间里冒出来,用讽刺的语气骂我。一个女演员路过,听到化妆间里的动静,走了进来。两人的矛盾立刻升级为群体冲突。
男主角问女主角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对他发火,女主角转过头看着我说:“因为你骂了她,她是我的朋友。”
我和那位女演员曾经在一次演戏练习中分别扮演第三者与原配,还互扇了好几次耳光,因为这次矛盾,我们一起退出了话剧社。
听说离开公司的老演员有的去当群众演员了,有的去演密室里的鬼,同期进公司的老演员中,只有佘颖还在等待当女主角的机会。
*我是根据此人的口头陈述写的,因此信息比较模糊。
- 结尾 -
撰文 | 刘岩
第三届非虚构文学写作大赛
为了推动非虚构文学的普及,我们再次携手数十家知名影视公司、出版机构、媒体平台,共同发起第三届非虚构写作大赛,寻找这个时代故事中的“当事人”。
竞赛评委:非虚构作家Peter Heisler(中文名何伟)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长风、作家袁凌、导演辛玉坤、编剧雷志龙。
奖项设置:一等奖:中篇小说1部(5万字以上),奖金10万元;二等奖:3名,各奖金2万元;所有入围作品将获得丰厚的版税报酬;故事猎人推荐作品入围奖励500元,推荐作品获奖的,奖励1000元。
投稿邮箱:tougao@zhenshigushijihua.com

